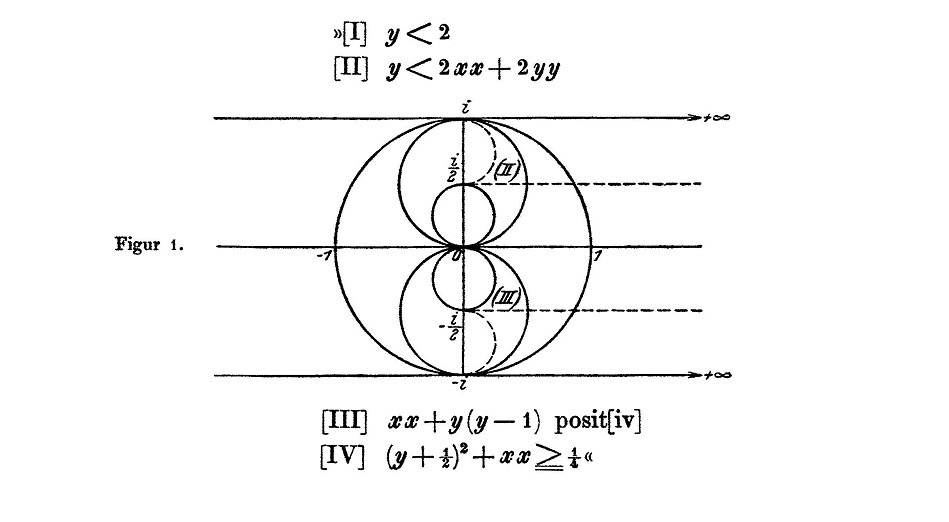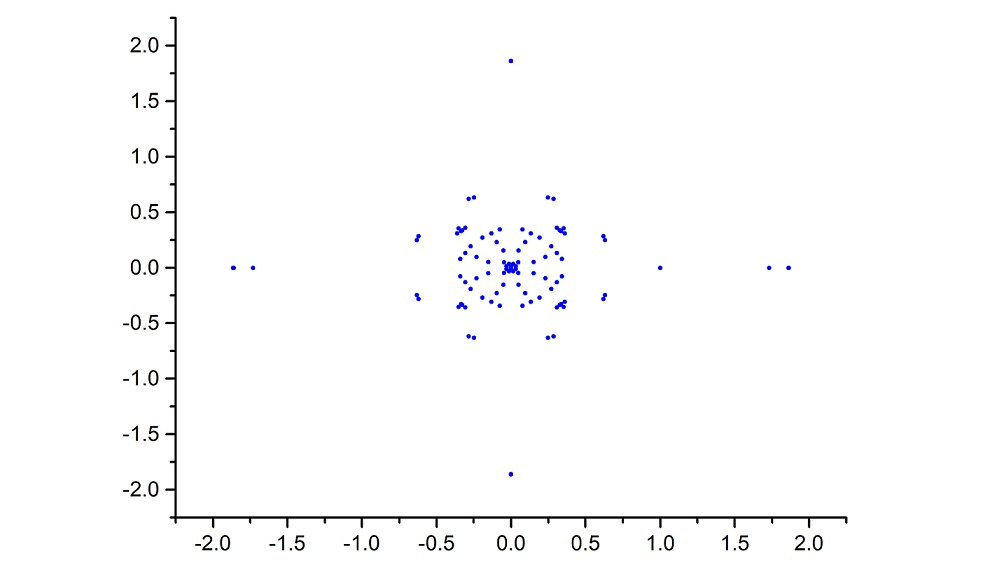屈原是科学家──人文与科学对话
诗人屈原也是个科学家?两千年前,屈原在气势磅礡的长诗〈天问〉裡,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,诘问天文、物理、哲学、人类学的奥理。浓厚的文学热度,包裹诗人对宇宙、自然的探索,也表现实证、理性、同行评议的科学特质。龙应台文化基金会「国际名家论坛」邀请德州超导中心资深主任暨中研院院士朱经武、香港大学教授龙应台比剑,看人文与科学电光火石的撞击。
龙应台:今天虽然名为对谈,但我希望把重点放在科学家的身上。朱经武教授曾荣获十个荣誉学位;六个荣誉教授的头衔;超过五百七十篇论文;二○○九年七月一日才离开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一职,回到休士顿投入自己一生的志业,就是他的物理实验。
朱经武院士生于湖南芷江,这裡是抗战期间重要的空军基地,飞虎队从此地起飞;抗战结束以后,协商受降的会议都是在芷江开的,朱教授也是空军的小孩。到了台湾,他在清水小镇长大,在清水的童年,他会把破铜烂铁收集起来做实验,他对清水的情感,使得他后来虽然离开台湾多年,却始终抱着深刻的情怀。
朱经武曾问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题目?小时候我读屈原的文章,当我读到〈天问〉的时候,虽然文字非常难懂,却忽然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,一个诗人在一篇文章裡面,气势磅礡的提出一百七十个问题,这些在我看来全部都是科学的问题,讲宇宙万象,开天闢地、从头说起。
我特别注意到,在人类早期的历史裡,尤其到我后来接触到西方思想史时,更有一个很深刻的发现,像屈原这样一个诗人提出科学的问题,在希腊的历史或早期的科学史裡,一点都不特别。因为,在西方的思想史裡,科学和其他学问从来都不是割裂的。
如果上网搜寻亚里斯多德的文章涵盖哪些层面,你会看到物理、生物、戏剧、音乐、逻辑、修辞、政治、伦理、动物学等等,科学与人文学不是割裂的。再往后走,你看达文西跨界跨到什么程度呢?数学家、建筑师、发明家、工程师、音乐家、凋刻家、植物学家、解剖学家、画家……。如果对达文西这样一个人去谈科学与人文之间有什么桥梁?在他们那个时代,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。对我而言,达文西《维特鲁威人》这张图几乎涵盖了从最柔软的人文到最硬的科学。
在香港认识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之后,我自己有一个撞击,就是我每一本书朱经武一看就懂,但是,朱经武跟我解释物理的、高温超导的两句话,我却怎么都听不懂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。我们一直在说无论科学家、医学家、经济学家,还是企业家,都要有人文素养,这个说法已经深入社会、没有人会去怀疑。但是,当我进一步认识像朱教授这样的物理学家时,我开始对自己有一种怀疑,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学的创作者,我的科学素养有多少?在哪裡?我发现,与我们对科学家、医学家、经济学家、企业家所要求的人文素养,不成比例。
从这个自我怀疑开始,让我们慢慢走到今天来谈论这个问题。
作为一个科学家,他的工作方式、品味、风格、想法,都由几样东西来决定。第一点,我想每个人做事都由他的经验、兴趣、教育来决定,这裡面取决于他的社会经验、人文素养、大环境的情况与时代的关係。
譬如,氢弹之父也是杨振宁先生的论文导师爱德华‧特勒(Edward Teller),他除了在物理、氢弹做了很大的贡献,更在美国国防扮演重要角色,同时,也是一位极端的反共主义者。特勒是在匈牙利毕业的,所以他对于文学、音乐、数学的修养都非常好,可以看出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多么的重要。
其实,不论是做科学或其他各种领域,最重要的,是看自己的兴趣在哪裡。我从小就对「电磁」很有兴趣,兴趣虽然重要,但是也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,决定朝向哪个方向走。
家父年轻时就一个人在美国读书,当时日本侵略中国,他就到各个地方演讲募款为中国空军买飞机,靠着个人募款,买了一百多架飞机。到了三○年代,他放弃一切回中国,他各诉我们兄弟姊妹,看着美国沿海的军舰与中国沿海的帆船,感受特别深,他觉得中国的贫穷是因为科技不够,所以,一直鼓励我们往科技发展。那是很单纯的一个动机。
但是,在我那个年代还有很多事情发生,影响我选择读科学。一个最起码的想法就是要经过科技报国。在我读中学时,杨振宁、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,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,因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拿到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奖。
以前,很多东方人觉得自己只能写写文章,科学则是由西方做的,杨振宁、李政道得奖使得东方的年轻人,特别是中国年轻人得到了信心。所以,很多年后有人问杨振宁,你觉得你在科学上最大的贡献是什么?他说,最大的贡献就是帮中国的年轻人找回了信心。
由于这点,我决定要做一些科技的东西。一九五七年,苏联释放人造卫星,美国吓得一塌煳涂,就设了一堆奖学金,因为这些奖学金使得很多外国学生可以去念书,我们读科学的到美国很容易拿到奖学金。另外一个原因,老实说要到美国读文学谈何容易,科学因为读的是公式,不论哪个国家都一样。
社会、人文的大环境会影响一个人。我跟龙应台讲,她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写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,其实做个科学家也是一样,必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,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
龙应台的《目送》出版时,我在回美国的路上看完了,我跟龙应台说,你这本书就像我在高中时读朱自清的〈背影〉。很多人看到父亲的背影时,没有办法写出深情的感受,但是,文学却可以做到。
所以,我常常说,做科学研究的人不应该只看到手边的东西,应该要看到更上层的东西。人文素养的确在人的思想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,可以使人有一种中心思想,有人称它是「信念」或者「信仰」。
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,他说,老天爷总是找最简单的路子走,使我产生一个中心思想就是「很多东西应该朝简单的做」。这些年来,我一直觉得大自然是很简单的,简单是非常美丽的东西。
所以,我常常跟同学及同事们讲,实验可以分为四大类,第一种也是最好的实验就是「很简单而且很有意义」的实验;第二种是「很複杂但是也有意义」的实验;第三种是「简单而没有意义」的实验;第四种是「複杂而没有意义」的实验。
人文,可以让我们大规模的释放对创新的想像力。爱因斯坦说「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. It is the preview of life's coming attraction.」世界如果一直向前走,想像力是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,这几十年来我在工作的过程中,总是希望不要跟着人家赶鸭子,希望走出自己的路,别人都走的例子,你最好避开。工作也需要冒险的精神,失败了也要承受责任与打击。
我是做高温超导的。我们是怎么能做出一些别人没做出来的东西?基本上,这裡面也有跳跃式的思想,当别人按部就班的走下去时,我们忽然转了一个方向,往别的地方走,简单的说,当时全世界做高温超导的人都向一个方向走,是物理的传统方法,先找出最好的材料,搞懂了之后才往下一步走。但是,我们却是在没弄懂之前,就跳了一步去思考。结果我和吴茂昆教授与同学们就做出来了。这是人文教导我们跳跃性的思维。所以,社会、人文、教育对一个人的工作、态度及工作的结果,是有极密切的关係。
龙应台:史诺(C. P. Snow)是英国有名的科学家暨小说家,同时也是政府官员,他在一九五九年时做过一场演讲名为〈两种文化〉(The Two Cultures),你很难见到一篇演讲,五十年后还被当作国际会议的主题来讨论。
朱经武给我的刺激,就是让我发现自己对科学的无知,在自我觉醒、自我批判的过程裡,我回头去看史诺这篇五十年前的经典演讲,他在文章裡提及常常在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聚会的场合裡,看到人文知识分子问科学家「你知道莎士比亚多少?」或者「你读了几本狄更斯的作品?」科学家如果没有读过或不知道某个作品,就会觉得很羞愧。
史诺在演讲裡提到,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冲动,想要问这些人文知识分子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什么?」把他们全部打倒在地,可是,人文知识分子即使回答「不知道」,还会觉得引以为荣。
史诺批判的是整个社会的决策者,大部分都是由非科学的人文知识分子所主导,这些人是对科学的知识与常识所知有限的「科学盲」,他说,这样的人怎么做决策?五十年前史诺就对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判。
我想问朱经武,在你所接触的科学家与非科学领域的菁英,史诺的观察是否也让你深有体会?还是你不赞同他的看法?
朱经武:一般来说,你讲的是对的。现在很多从事经济、法律或各种领域的政府领导,表面上,是不需要科技知识的,但这是很危险的情况。因为,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,它的进步必须要靠科技的发展来维持繁荣,这是很重要的,所以,我同意你这一点。
不过,社会慢慢在变,史诺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,勾勒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很大的差别,后来有些人也批判他这场演讲。有的人引用史诺的看法,觉得科技发展得正当,促使社会向前走,人文就发展出来了,是科技的一部分,但是,大家也知道,人文其实可以主导科技的发展。反对者的说法是史诺勾出了两者的差别,使得科学与人文知识学者互相对立,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另一方面,从某个程度来看,六○年代、七○年代,人文知识分子确实也有狂妄自大的心理,使得科学家受不了。
这些年来,问题还继续存在。但是,有些人也慢慢意识到,并开始经过不同的途径,慢慢的减少两者之间的不了解,因为,社会的进步一定要这两部分的知识分子互相沟通,才能够向前走。
龙应台:前几天,我和朱教授为了这场演讲做功课。五十年前,史诺给了科学家有关人文常识的题目,也给了人文知识分子有关科学常识的题目,我看了吓坏了,因为,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「热力学」,更不知道它的「第一定律」、「第二定律」是什么。
所以,在做功课时,我提出五个人文基本ABC,看朱教授能答对几个,然后,朱教授开五题他认为的科学基本常识,彼此测试,我把这十个题目拿出来给大家玩玩。
先看我考朱经武的题目:
一、《道德经》是谁写的?
二、曹雪芹写了什么?
三、马克斯是哪国人?生在什么时代?
四、谁写了《浮士德》?
五、毕卡索是做什么的?
接下来,朱经武给了我说是与前面五题对等的题目:
一、James Watson做了什么?
二、人为何不能把自己抱起来?
三、为什么树下的光影是圆的?
四、如果你坐在时速一百公里的火车裡,拿灯;另一人静止不动,拿灯。同时开灯,二公里外有人在测光,请问哪一盏灯光先到?
五、牛顿第二定律是什么?
我打死不相信,这突显了科学家不知道什么叫简单吗?还是突显了我这个人文知识分子所有的「科学盲」。两种文化怎么沟通?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大的鸿沟?
如果我们两个都同意,确实有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了解程度,与我们要求科学家具备人文素养的程度不成比例的现象,我想问朱经武的是,So what?有什么不好?
朱经武:这个社会科学家还是少数,但是在社会发展裡,管理阶层很多都是人文知识分子负责,但是我们也知道,整个社会向前进时,科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
我们看看过去一百年来的变化,《封神榜》上面说千里眼、顺风耳,现在都实现了,人类的财富增加了,各种东西都向上提升,如果你追究它的原动力,既非经济也非政治,而是科技。所以,科技发展对于维繫社会向前走,是非常重要的。
但是,这些年,社会的价值观慢慢在变,大家不做真实的东西,去做虚拟的经济,才会有金融海啸,所以,欧巴马在几个月前讲了一句话,他说,当金融海啸过去以后,华尔街的影响力会减少一半,最后会有很多年轻人把智慧投入社会,做创新的工作,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。
去年,也是在龙应台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,我与杨振宁先生有一段对话,当时正值金融海啸发生,杨先生说了一句话,他说:「今天在这裡大家担心的都是金融崩溃,金融海啸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,但是等到十年、十五年后,真正要担心的问题是社会对科技的漠视。」
几年前,我有个朋友在英国开会,当时的首相召集一个会议,找了很多大公司的总裁与政府官员参加,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,他说,今天我们的社会那么富足,到底是什么原因?现场提出有很多答案。他却说,不对,应该是麦克斯威尔(Maxwell)电磁波的四条公式。
你可以想象,科技对社会继续发展到底有多么重要,而创新发明正是持续的步骤,因为,今天的发现,明天就变成常识。要维持领先的竞争力,一定要不断有新东西产生。
所以,我觉得,整个社会应该对科技有欣赏、了解的能力,并不是要每个社会的公民都变成科学家,而是希望他们支持科学家做新的发明,因为,这些发明最后都会造福社会人群。